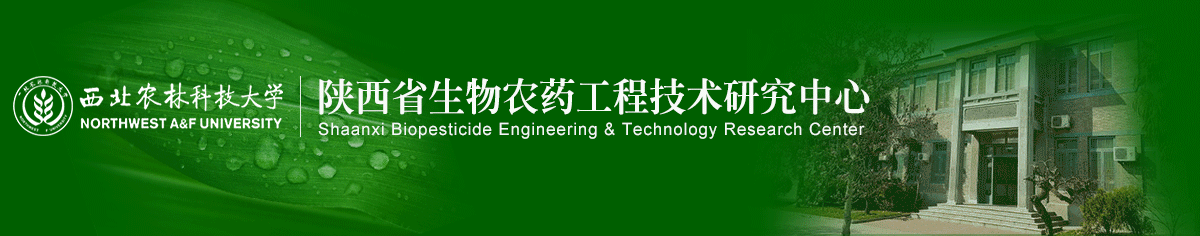大写的“人”上篇
发布日期:2010-11-15 来源:农业科技报 作者:牛宏泰 点击量:
张兴,男,1952年生于陕西周至,1974年毕业于原西北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后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陕西省教学名师。
可以说,张兴是在苦楝树下长大的。饱经沧桑历尽人间疾苦的父母亲,在他之前已生有三儿一女。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有点多余。让他记忆最深的是,当他刚刚懂事时,看到的是每逢断粮缺钱就抱头蹲在屋角长吁短叹的父亲,长年靠吃止痛片支撑身躯干家务的母亲,有三个无钱娶媳妇且其中两个作了“上门女婿”的哥哥,还有从小背着他、看护照料他的姐姐。为了照料他,姐姐直到9岁才上小学,带着刚刚5岁的他去学校报名。和蔼可亲的女老师见当时比课桌稍高一点儿的张兴聪明伶俐,便逗着问他愿不愿意上小学。没想到一句不经意的逗笑话竟像吉祥的口彩,奠定了他的人生之路——“我不想上小学而要上大学”。看他十分机灵可爱,几个老师一商量,决定让他提前上了学。他姐弟同班上到四年级,他父母见他和姐姐已经能分辨人民币上的字,便强迫他和姐姐中途辍学。此时张兴上学念书正带劲,哭死闹活非上学不可,父亲拗不过他,只好由他。
由于张兴天资聪颖,学习用功,跳级上完小学,11岁就考入陕西周至县终南中学上了初中,老师见他不同一般,逢人便说集贤村恐怕要出大人物了。
陕西周至县终南中学离他家15华里,因为他年龄小不能天天步行往返,11岁的他便背上铺盖当了住校生。那时节中国大地上的3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家里缺衣少粮,他每个星期六回家,背18个蒸馍,星期天天黑前赶到学校,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中、晚饭,顿顿全吃白开水泡馍。唯一的佐餐品就是从家里带点儿食盐,每顿吃白开水泡馍时用筷子头蘸一点食盐加进去。最奢侈的是偶尔从家里带些干辣椒面,吃饭时给白开水泡馍里加一点,那就是过年般的享受了。可辣椒却有促进胃肠消化的功能,使得他胃口大开,平均一顿一个蒸馍压不住饥饿,有时就不由得多吃一个半个。但带的馒头总数有限,这顿吃了下顿就得少吃或不吃,饿了也只能硬撑着。长期的食物单调且营养不良,使正在长身体阶段的他过分消瘦,饥饿常使他头昏眼花,有一次竟昏倒在地。同学们扶他起来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脸色惨白无言以对。
那段时间,他姐姐在家里缺衣少粮的情况下,每次蒸馍馍总是预先留够他的18个馍馍,其余的才留给全家人。有一年青黄不接的时节,他从家里背到学校去的榆树叶粉和面捏成的蒸馍到星期四就长出了黏乎乎的白丝丝,掰开馍馍白丝丝扯得老长也断不了,他只好向老师请假回家换馍。当他忍着碌碌饥肠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回到家时,只见全家人都躺在土炕上,原来家里已断粮好几天了!听他说把馍馍带回来了,也顾不得发霉变质,拿出来在铁锅里加上水热透了,狼吞虎咽般分着吃了。
那天晚上,他独自走到茅屋外的苦楝树下,抚摸着挺拔的树干,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他觉得自己之所以那样喜欢苦楝树,恐怕是因为自己的苦命和苦楝树的苦味有某些相似之处的缘故。
1966年,张兴初中毕业了。由于家境贫寒,他当时没有报考高中,而是报考了一所中技学校(中技学校不收费),虽然这所中技学校录取了他,但由于“文革”开始了,他就无法进校学习,只好辍学回家务农。
可他是个勤于观察、善于思考的有为青年。他发现自己家茅屋外的苦楝树以及周边庄稼地的苦楝树下,即使是炎夏酷暑,湿热蒸腾,只要有苦楝树叶遮蔽,蚊蝇、小虫很少来树下烦人。许多当地农民一见菜地里有虫子为害,就折几把苦楝树枝扔在地里,常常会起到灭虫的效果。
这类事儿诱发出他极大的兴趣。他折来苦楝树枝放在口中咀嚼,除了感到苦涩外再也无法深入探索。每逢阴雨连绵无法作务农活时,他总喜欢躺在土炕上琢磨这些事儿。可最终他还是失望了。因为他感到自己所学的知识还远远不足以搞清其中的奥秘。
然而,机会终于降临到他的身上,而且是那样神速、别无选择又极具传奇色彩。
那是1972年春天,推荐上大学的难得机遇,竟然降临到他这个很少有人注意的人身上。全乡只有一个名额,他也不明不白地超越众多的“对手”被选中进入当时的西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实现了他5岁那年的“口彩”。
这是张兴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当他极其顺利地坐进西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植物保护专业的教室里,他才觉得这段时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是真的,不是梦!他也才得知这里人才济济,名家辈出,是全国有名的农业“花园学府”之一。他想,命运有时还真有“天遂人愿”的时候,自己正苦于探索植物杀虫奥秘不得要领、难以问津而无法进展时,自己竟鬼使神差地真有这么一个学习植物保护知识的机会。植物保护,顾名思义,肯定是学习和研究植物保护知识和技术的。因此,除了认真学好每一节课,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不论大本小本、厚本薄本,只要他觉得可能和植物保护沾边,抱起来就啃,尽情地咀嚼、吸吮着科技知识,同时记下了一本又一本笔 “苦楝又名楝树,楝科,落叶乔木,高可达20米,春夏之交开花,花淡紫色,圆锥状聚伞花序,花丝合成细管,紫色,核果球形或长圆形,熟时金黄,俗称金铃子。因其子小如铃,熟则金黄,故名。主要分布在我国山西、河南、陕西以南地区。印度及东南亚亦有分布。多生于低山、平原。最喜光,生长快。木质坚硬,易加工。可供家具、乐器、建筑、舟车、农具等用。种子供药用。花、叶、树皮、根皮亦入药。又为行道树、观赏树及海防林树种。它高大,树干直,浓荫如伞,树冠舒展飘逸。开花时节,香而有苦味,因而香得特别,香得持久。亦能在秦岭及其北麓生长。秦岭北麓一带人称这为‘苦苦树’。这是因为,生长在秦岭北麓及其丘陵地带的苦楝树,因昼夜温差大、体内贮存的水分少,因而划破树皮流出的汁液特别苦。而环境条件愈差,树皮流出的汁液也就益发苦不堪言。
苏东坡在《格物粗谈》中写道:端午取苦楝子,碎投厕中,不生虫。
“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楝花铺席下,杀蚤、虱……
哦,苦楝树下走出的张兴,时刻没有忘记对苦楝树的深情。他清楚地记得,当他背着铺盖上大学时,是手抚苦楝树干、眼含热泪、怀着深厚的眷恋之情离开家乡那片生他养他的一方水土的。当时母亲已年过七旬又体弱多病,父亲已80高龄,腰身佝偻,风烛残年。两个哥哥当了“上门女婿”,寄人篱下,姐姐已经出嫁,另一个哥哥成家后已分家另住……。两个老人谁来照顾?这是他的最大担心。多亏了古风淳朴厚道的家乡父老乡亲答应帮衬,他才得以一步一回头地踏进高等学府的大门……
哦,走出图书馆的他,来到校园里的一棵苦楝树下,抚摸着它干瘦但却硬朗的树干,被它的可贵的品格深深感动了!
很快,张兴大学毕业了。由于他品学兼优,经过学校层层选拔,他被留校任教。苦楝树下走来的张兴,走上了大学讲台。
1977年,和煦的春风吹化了冰封许久的祖国大地,历经磨难的人民共和国,重新恢复了大学招考制度。1978年,又恢复了研究生招考制度。看到这一喜人景象,张兴不由得动了心。他一边认真工作,一边不失时机地进行报考研究生的准备。
1979年9月,经过严格考试筛选,张兴考中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昆虫毒理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委员赵善欢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攻读方向为昆虫毒理学。
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张兴盼望着自己能考个好成绩,争取被录取。当正式录取通知书拿到手上时,他是又喜又愁,悲喜交加。喜的是终于如愿以偿考中硕士,悲的是年老的母亲和妻子儿子在农村老家,生活清苦不说,自己远去华南,他们谁来照顾?更何况,自己翻遍所有衣袋,连买一张去华南读学位的火车票的钱也凑不够。这个状况,自己的家人生活怎么办?
越想越愁,越想越难,经过无数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平静下来,他打定了主意——放弃读硕士。
硕士报到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张兴没有一点动静。他周边的老师和同事们都感到奇怪。一个个用询问的眼光看着他。他只装作没看见,仍然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备课、准备实验、做实验。
硕士报到的日子已经过去了10多天,他仍然无动于衷。老师和同事终于忍不住了,问他怎么还不去报到。他淡淡地回答:“不去了?”有的人好心地劝他,他不为所动。有的人也表示支持他的选择,但又表现出各种婉惜之情。
这天夜里,系党总支书记王建邦老师猛然推开了他住的宿舍门。当时他正在灯下备课。
王建邦书记手里拿着一沓钱,语重心长地对张兴说:“我知道你的脾气,也知道你的性格。你是个硬汉子,宁折不弯。从来都不肯张嘴求人。你之所以至今不去报到,是因为没有买一张车票的钱。”
王建邦书记拿着那沓钱对他说:“我替你写了份困难申请,从系里和学校领到130元困难补助款。我知道你的硬气劲,所以替你签的字。你知道,系里困难补助的最高额度是30元,学校困难补助的最高额度是100元,合起来就这么多。但可以帮你解决买一张去广州的火车票。你还是去吧,机会实在难得啊!学校支持你去深造,没有别的要求,只是希望你毕业后能回来工作。你清楚,咱们缺化保老师啊!”
听到这里,张兴的双眼湿润了,他咬了咬嘴唇,十分矛盾地接过王建邦书记递过来的130元钱,紧紧握住王建邦书记的手,眼泪再也止不住了,顺着腮边一串串流了下来,一句话也说不出。
山重水复疑无路
张兴挟着一身大西北黄土高坡风沙黄尘来到华南农业大学昆虫毒理研究室不久,以治学严谨、要求严格、待人严肃的“三严”作风而著称的赵善欢教授慧眼识英才,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敏而好学、纯朴执着的北国青年张兴。
在羊城求学深造的头3年,张兴很少回家。一则是由于自己的确囊中羞涩,拿不出多少钱买火车票;二则是由于他在研究实验中发现某些植物对害虫有致其拒食和不能正常生长发育的作用。他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个富有魅力的自然之谜。似乎是一种直觉,他朦胧中觉得苦楝很有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植物。但科学研究是十分严肃、严谨、严格的,来不得半点“想象”和“跟着感觉走”,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试验材料和科学数据。为此,他住进实验室,以便于观察、分析、试验,同时也为更节约时间。他还在几小片空地上种了些青菜,自己抽暇在实验室做饭吃,可以节省点费用,省下尽可能多的钱寄回家里,贴补家用,养家糊口。而此时,他的父亲已经过世,垂暮之年的老母亲长年卧病在床,只字不识的妻子任凤香除了侍奉老母亲,还拉扯着一对儿子……
当赵善欢教授耳闻目睹了张兴的这些情况后,不禁感慨万千,对这个勒紧裤带孜孜求学的上进青年更加青眼相看,更加悉心地指导。
在斡旋硕士论文阶段,张兴看到国内外刊物尤其是国外刊物上关于印楝的研究报道很多,便选择印楝作为主攻目标。因为印楝是世界热门植物,已经取得较大研究进展,并召开过好几次印楝国际学术会议。
但是,必须亲自做实验,才能作出最后的结论。通过一段时间的实验研究,他得到的数据证明,印楝中的印楝素药用效果最为理想。在印楝素对昆虫致毒机理的研究中,他所得到的“其为一系统性致毒作用”的结论,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重视与认可。这一点,也与国外众多的研究结果趋于一致,极富开发价值。可是,此时他却发觉自己走投无路了!
原来,印楝主要在印度及东南亚各国广泛分布,属亚热带树种,非洲及南美洲也有分布,但在我国尚未发现真正的印楝树种。他亲自参加了此前海南和广东的印楝引种,一者数量远未形成规模,加之引进的印楝树树种树冠生长太大,不抗台风,多年后宣告失败了。而国外的印楝研究早已捷足先登,美国已有印楝杀虫产品登记注册,印度的印楝产品也已进入国际市场。如果我国步此“后尘”,落后一步不说,仅原料进口一项,其费用之高已不难想象。
一下子,赵善欢教授和张兴都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之中。
此时的张兴,仍然住在实验室中,除了做实验,还是自己种菜,自己做饭。而此时的广州早已不是数年前的广州,消费水平之高,更不是他的工资水平所能承受得了的。那时节,他每月只有52元工资,而且需要用购粮本去买。为了生存,他只好硬着头皮借家在广州的同学或老师的粮本,去购买当地最便宜的面饼,勉强维持……
生活的困窘加上事业上的困窘,两面夹击着张兴这个从北国苦楝树下走来的汉子,他陷入徘徊之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天夜里,他独坐灯下,陷入苦苦思索之中,不知不觉间伏在书桌上,朦胧中又一下子惊醒,一道灵光闪过脑际,他想到是否可用川楝代替印楝?想到此,他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和轻松感,急于想找赵善欢教授交换意见。当他一头冲进室外浓浓的夜幕之中时,才意识到半夜已过,太晚了。借着路灯看一下手表,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兴奋异常又急不可耐的张兴只好重返实验室,在一沓稿纸上盘算起下一步的研究方案来。
其实,此时的赵善欢教授同张兴一样,也无法入睡。这段时间,赵教授同张兴一样焦虑。也许是一种心灵感应或“英雄所见略同”吧,赵教授也想到了用川楝作为印楝的替代品,在中国开发植物源农药。他此时也正急于想找张兴交换意见,也同样是因为夜已过于深沉,未去打搅。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张兴一步冲进了导师赵善欢的寓所。师生二人一见面,抛却了惯常的礼仪,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同一个思路——真正的“一拍即合”!
可张兴却怎么也没有料到,他又一次陷入两难境地。
人的思维,常常有一种“定势”。张兴这次研究与探索的曲折与坎坷,可以说是人的思维定势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影响所致。
按照国外和他自己从印楝果实中提取和研究印楝素的方法,他花了将近一年半时间,从我国广泛分布的苦楝、川楝的果实和叶子中提取杀虫物质,同时配制了一批杀虫试验品。可是费尽千般周折、万番艰难,他不仅未从中找到印楝素,而且提取物的杀虫效果也不理想。用苦楝和川楝替代印楝的思路,几乎化为泡影。他又一次陷入困境之中。
科海探险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珍。经过一番艰苦的探索、分析、试验和研究讨论,张兴果然不负导师赵善欢教授的重望,接连在国内外有关刊物上发表了植物源农药研究方面有分量的论文,引起学术界同行的普遍关注。
但是,凡是张兴与导师赵善欢教授共同署名发表的论文,稿费赵教授一分都不肯要,全给了张兴这位有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的高足。以至由此以后,张兴每一忆及或谈及此事,就禁不住无比动情地遥望南天,摘下眼镜,一遍遍地擦拭镜片!
糟糠之妻不下堂
随着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有名的羊城广州,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议论中,即使是在张兴的家乡陕西周至县集贤村,虽是穷乡僻壤,却也议论迭起。原因是张兴在广州,不仅很少回家,竟连书信也少见。有人交头接耳说张兴忘了任凤香。有人说任凤香大字识不了一箩筐,土得掉渣,张兴是研究生,早就想甩了另娶。何况如今远走高飞,到了广州那“花花世界”。有的甚至说在广州亲眼见张兴手挽相好的,连孩子都抱上了。
谎言说过三遍,就有可能成真。这些风言风语越说越真,竟连死活都不肯相信的任凤香也有点相信了。她无论怎样也在家里坐不住了,下决心南下广州去找她的“陈世美”。学一学当年的“秦香莲”。
她含着满眼的泪水,在灯下给张兴赶缝了“最后一套衣服”,牵上小儿子,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南下的火车上坐着任凤香和小儿子。小儿子不知道大人的心思,早就睡着了。可任凤香却仍然心潮起伏,不知此行是福还是祸,因而难以平静。她觉得张兴是大学生如今更是研究生,自己能跟他过这么多年日子已经知足了。而自己为张兴侍奉老人,生育两个儿子,缝补洗理,撑持家务,也算对得起张兴。自己虽不识字但却懂礼。此行一是为了探个究竟,以了却心中渴念,二是平息一下自己心头的忐忑。如果传言是真,自己不会真像秦香莲那样去找包公断案,而是给张兴留下一个儿子转身就走……
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抛头露面去广州。心急如焚的她顾不得欣赏沿途南国风光,悄没声息径直来到华南农大,轻手轻脚地推开了昆虫毒理研究室的大门,朝里探头一看,室内仅是张兴一人正在挥汗如雨地忙碌着赶写文章,不见有什么女人、孩子之类。
正在专注地埋头写作的张兴猛一抬头,见是妻子和小儿子站在自己面前,高兴地一下跳了起来,揽过小儿子亲个不够。
妻子不冷不热:“不认得?”
张兴不明就里:“咋不认得?”
夜晚来临,任凤香留了个心眼。张兴着意为她安排的住处她死活不去,非要“守着”张兴。其实是想看个“究竟”。心想自己绝不是那个秦香莲。
一连3个晚上过去了,一切平静得出奇。只见张兴每天从早到晚只顾拼命工作,并未见有什么“公主”、“阿妹”的上门来打搅。任凤香疑惑不解。有天夜里便不冷不热地问张兴:“是不是我们娘儿俩来了,你那相好的不敢露面了?”
“啥相好的?”张兴一头雾水,莫名其妙。转念一想,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妻子带儿子此行来到华南的用意,不禁朗然而笑:“你想到哪里去了!相处这么多年,你还信不过我?”
“那你为啥连着几年都不回去?”妻子毫不放松,紧追不舍。
张兴一听,低下了头:“没有钱呀。与其把钱都交给铁路和火车,倒不如寄给家里让你和娘、孩子们过得宽余点。”
一提到钱,妻子似乎理解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张兴每月的工资有多少钱,她当然清楚。但她仍有疑云:“那写封信回去总可以吧?”
“写信?写信不是明摆着为难你和家里人吗?再说我也忙,事儿太多,又何苦让你们作难呢?”
说到这儿,妻子听到的所有风言风语和猜疑顷刻间冰释了。自己只字不识,母亲更是如此,两个孩子都小。真要有信,还得求人念给她听,多难为情。
理解出真情。亲眼看到张兴对自己及全家人的一片爱怜、体察之心,作为一个妻子,只有更加敬护张兴的分儿。
任凤香与小儿子在张兴那儿住了半个月之后,不顾张兴的再三挽留,执意要带着小儿子返回。家里还有一老一小两口人让她无时无刻不牵挂和忧心啊!加之张兴太忙,她不忍心为自己和孩子让张兴分心,何况老婆母有病在家,自己出门多日,老人家肯定也是忧心如焚啊。
张兴送妻子和小儿子来到广州火车站,妻子和儿子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列车停在站台上尚未启动的那一刻,任凤香从车窗口伸出头来低声对张兴说:“我看你师兄师弟们每个人身边都有个年轻漂亮的大学生、研究生作伴。你一个人在广州太孤单、太可怜。你如果愿意,给我句话就行。我不怪你。能和你过这么多年,我知足了。”
一声汽笛长鸣,铁轮隆隆启动,越转越快。张兴只觉得月台和自己的身体在同时颤动,喉咙哽咽,眼圈潮湿。他随着火车的加速,追赶着妻子和儿子所在的车窗口:“你别胡思乱想。你替我上养老母,下育儿子,我才能安心读书,静心研究。你要一句话,我就给你一句话。我们要过一辈子!”
妻子扶着车窗,泪水奔涌而出,泣不成声。
铁龙轰鸣着驰向远方!
倚天万里须长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清晨,一辆满载着几千斤鲜嫩黄瓜的拖拉机驶进某市一家蔬菜市场。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时间不长,吃了这家卖的黄瓜的人,有数十人丧命,数百人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医院的化验结果表明,这些黄瓜上市之前刚刚喷洒过有机磷剧毒化学农药……
某年夏天,一对新婚夫妇到南方某城市度蜜月。当他们旅途中口渴难耐时,便就近在一个蔬菜摊上买了几斤鲜红的西红柿,用卫生纸擦了擦便吃了起来。可他们还未返回所住的旅馆,两人相继栽倒在大街上。经路人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检查,发现他们两人的胃中尚未消化的西红柿中含有剧毒农药……
看到这些报道,作为研究新型植物源杀虫剂的张兴心里真不是个滋味,不由得从心里更加铆足了劲儿。
新型植物源杀虫剂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才兴起的世界性热门研究课题。张兴的导师赵善欢院士1979年赴德国参加了这方面的世界专门会议,受到很大启发,并紧紧抓住机遇,回国后在我国科学界首次提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研制新一代无残毒农药势在必行。要想不让类似悲剧发生,要想让我国人民延长寿命、后代聪明、生活幸福,要想让我国瓜果蔬菜跻身世界市场,在农药研制、植物保护方面必须先行一步,必须要有这个超前意识。
因此,在赵善欢院士的指导下,张兴将他的硕士研究论文题目确定为《楝科植物杀虫剂对几种害虫拒食和抑制生长发育的作用》,并尽力加快研究进度,查资料、找药典、做实验、取数据、摄实物……夜以继日,孜孜以求。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苦心孤诣地探索,张兴终于摸清了楝科植物对某些害虫具有抑制其生长发育、改变其味觉器官的感觉而对农作物产生拒食作用等机理之所在。当年在故乡的苦楝树下发现的有趣现象,在科学之光的映射下,现出了清晰的逻辑关系。因而当他登台毕业答辩时,那严谨的科学依据、大量的实验数据、翔实的试验材料、真实的实物照片、流畅的叙述文笔,令答辩委员会的专家教授们大为赞赏,一致同意评为优等,并在华南农业大学全校研究生和导师大会上作了论文答辩示范讲演。
眼看着这位刻苦自励、勤奋好学、科学求实而且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得意弟子戴上硕士帽即将告辞北归的时候,学识渊博而又以“三严”著称的院士赵善欢教授动心了,与弟子张兴展开了一场“攻心战”——专门约张兴到自己办公室谈话。
张兴估计导师可能与自己谈未来的动向。但他也知道,导师太忙,谈话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在平常,赵院士不论与谁谈话,最长也没超过20分钟。张兴清楚地记得,与赵院士同一列火车赴前苏联留学的一位同行和同学,因多年未见,前来找赵院士,赵院士只答应谈5分钟时间。结果真的就只谈了5分钟。
没想到,导师这次与自己的谈话破天荒地超过了4个小时——整整一个上午!
张兴来到导师办公室,赵教授开门见山,劈头就问张兴:“硕士毕业后有何打算?”
“回我的母校去!”张兴的口气毋容置疑,也不假思索。因为在此之前,赵先生也曾多次对他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他一直都是这样回答的。
“不可更改吗?”赵教授再次逼视着张兴。
“似乎没有什么可更改的。”面对严师的锐利目光和咄咄逼人的气势,张兴的口气稍有改变,但仍绵里藏针。
赵教授板着面孔,给他指出了3条出路,供他选择:1,留校——留在华南农业大学任教;2,分配去广东昆虫研究所工作——因与华南农业大学不远,两边联系和合作方便;3,马上送你出国,暂时不毕业——这可免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张兴心想,留在华南农业大学,留在自己尊敬的导师身边,留在南方大都市,这无疑是自己这辈子的福分,求之不得。但他忘不了故乡的苦楝树,忘不了离开西北农大前夕学校和系里领导、同事的依依深情。尤其是王建邦书记替他写困难补助申请并代他签字领取,雪中送炭般及时送来130元钱,才促使他最终下决心南下羊城。更何况大西北广袤而辽阔,急需一代代人才尤其是科教人才在此扎根、奉献和建设。出国也算一条路,当时很多人都是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的好事。但他觉得从事植物源农药研究,在国内搞比去国外学更便捷。这一点,导师比自己更清楚。因此,导师所说的三条路,其实说到底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留在华南。如果这样,他将无颜面见西北父老和自己的母校。因此,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恩师说:“我还是得回西北去,我的根在西北。”
赵教授不解地问:“岂不闻‘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不等张兴接话,赵教授又说:“你是不是担心你爱人和大儿子的工作安排?这个,我已替你想过了。华南农大会作出很好的安排。”
见张兴并没有答应的意思,有点出乎自己的意外——因为在当时,能安排农村户口的妻子和儿子两个人到一个大城市工作,那简直是天大的好事,无论是谁都会感激涕零的,而张兴似乎没有动心。赵教授接着说:“这个事你尽管放心。作为一校之长,我说话岂能不算数?”他似乎觉得张兴可能不大相信这事儿能办成。
张兴:“赵老师,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担心西北……”
赵教授不等张兴把话说完,断然地打断了张兴的话头:“这个你不用担心。西北农业大学不同意的话,我来做工作。你对母校有感情,我不让你出面。”
见张兴仍未答应,赵教授略一思忖,又说:“这样吧,我现在就给农牧渔业部领导打电话,让农牧渔业部领导出面先做做你母校的工作。”说着,不等张兴答话,就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要通了农牧渔业部,说明自己的研究室需要将张兴留下,请求部里出面做做西北农业大学的工作。张兴隐约听电话里不知是部里哪位领导似乎已经满口答应了。
张兴的头脑十分清醒:“赵老师,我,我不大适应这里的气候……”
赵教授不以为然地:“气候?你在这里3年了,气候不是问题!你妻子和两个儿子,来了后也会慢慢适应的。在华南工作的北方人多得很,哪个不适应了?”
张兴:“我母亲恐怕是难以适应的。”
“我知道你是个大孝子。老人的事,实践了才能下结论。别把结论下得太早了!”赵教授没想到张兴会这样执拗,不由得动了怒,终于和他“翻了脸”。
最后经农牧渔业部出面从中调停,才达成了一项折中的方案,由西北和华南两个农业大学共同签署了一份合同:张兴必须每年半年在西北农业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另外半年时间在华南农业大学从事新型农药研究。在两所大学的身份都是教师。签署日期为1982年10月。
1983年2月底,张兴带着南国求学的丰厚收获,一头扑进了魂牵梦萦的苦楝树下大西北黄土地的怀抱。手抚故乡的苦楝树,张兴在心里默默地与黄土地对话:你的儿子回来了!
在西北农业大学,张兴一边代课,一边探索,研究更加艰深的课题。然而,“初学三年剑,泰山不可当。再磨三年后,不敢试锋芒。”他原以为3年硕士学习,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以后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工作,不会有太大的障碍。然而,事实却让他一次次失望,他越来越深刻地体味到,自己仍然需要知识的补充。因此,他就进一步拼命地汲取知识的营养,认真备好每一节课,同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不断地开阔自己的视野。
他回到西北时,已经离春节很近了,只剩两三天时间。可大年初一刚过,他就一头扎进办公室和实验室,又是备课,又是做实验,还要加班加点整理论文。到这时,他才真正心领神会了“活到老学到老”这句古训的深刻含义。
第二年7月,他刚代完西北农大应代的课,又立即启程南下,按照两校的合同,去华南农业大学履行另一半诺言,继续开展新型杀虫剂的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张兴研究新型植物源杀虫剂,最初是从苦皮藤、雷公藤、鱼藤、黄杜鹃等植物的筛选开始的。经过对众多植物杀虫活性物质生物活性测试,并对其有效成分的对比试验和分析其效价及开发应用前景的过程中,先后筛选了150多个植物品种,其中有开发价值的就有近二十种。其中楝科10多种,还有豆科、桉树等。在1984年召开的全国植物源杀虫剂专业学术会议上,他讲述了自己在赵善欢院士指导下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与关注。
1984年3月,他又得返回大西北,履行自己的另一半诺言。而当他站在家人和同事面前时,人们已不敢认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脸瘦如刀背,身型像细虾……,简直成了另一个人!
原来由于前段时间在华南,时间紧,任务重,他的研究“胃口”又过于大,简直忙得他焦头烂额,饭是有一顿没一顿,又天天熬到深夜,身体怎能不垮?
为了能在赵善欢院士指导下悉心从事新型植物源杀虫剂的研究,也为了进一步给自己“充电”,他决定听从恩师的劝告,报考赵院士的博士研究生。结果一考即中。此时,西北农业大学决定送他出国深造读博士。面对又一个“两难”选择,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选择了在国内读博士学位。为了深造、工作两不误,也为了防止再有新的“麻烦”,他决定放弃读全脱产的博士研究生,而自动请求读在职的。后经当时的农牧渔业部再次从中协调,并发文确证,才终于办成了。许多人对他的这一系列“选择”大或不解,他的理由却很简单:力争在祖国的土地上拿出属于中国人的新型植物源杀虫剂!
1985年7月13日,他带完这一年在西北农大的最后一节课,于7月15日再次南下华南。
一到华南农业大学就拜见恩师赵善欢院士,他不等喘一口气,对恩师提出了自己的3点想法:一是继续从事楝科植物杀虫剂的研究;二是研究几种新发现的豆科植物杀虫剂;三是攻下利用烟草工业废料研究植物杀虫剂的难关……
独具慧眼的赵善欢院士不等弟子讲完,双目放光,满意地看着自己的得意门生,当即决定:继续从事楝科植物杀虫剂的研究,杀出一条血路来,唱一曲中国人的志气歌!
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他发现我国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利用川楝提取物驱蛔虫。由于当时我国医疗卫生状况较差,人们也不大讲究卫生,约有70%的人感染了蛔虫。起初人们只知道利用中草药山道年驱蛔虫,后来周恩来总理指示重庆中药研究所研制中国人自己的驱蛔虫新药,科研人员经过艰苦探索,发现川楝树皮中提取的川楝素驱虫效果特别理想,便动员四川等地发展川楝种植业,1955年即开始工业化生产,很多小厂都可生产这种驱虫药片。
梅花香自苦寒来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2年,张兴“不合时宜”地出生在距我国道教圣地陕西楼观台5华里处的周至县集贤村一户世代务农的人家。几间茅屋在瑟瑟寒风中向人们诉说着他家境的贫寒。茅屋旁有几株秀丽挺拔的苦楝树。 可以说,张兴是在苦楝树下长大的。饱经沧桑历尽人间疾苦的父母亲,在他之前已生有三儿一女。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有点多余。让他记忆最深的是,当他刚刚懂事时,看到的是每逢断粮缺钱就抱头蹲在屋角长吁短叹的父亲,长年靠吃止痛片支撑身躯干家务的母亲,有三个无钱娶媳妇且其中两个作了“上门女婿”的哥哥,还有从小背着他、看护照料他的姐姐。为了照料他,姐姐直到9岁才上小学,带着刚刚5岁的他去学校报名。和蔼可亲的女老师见当时比课桌稍高一点儿的张兴聪明伶俐,便逗着问他愿不愿意上小学。没想到一句不经意的逗笑话竟像吉祥的口彩,奠定了他的人生之路——“我不想上小学而要上大学”。看他十分机灵可爱,几个老师一商量,决定让他提前上了学。他姐弟同班上到四年级,他父母见他和姐姐已经能分辨人民币上的字,便强迫他和姐姐中途辍学。此时张兴上学念书正带劲,哭死闹活非上学不可,父亲拗不过他,只好由他。
由于张兴天资聪颖,学习用功,跳级上完小学,11岁就考入陕西周至县终南中学上了初中,老师见他不同一般,逢人便说集贤村恐怕要出大人物了。
陕西周至县终南中学离他家15华里,因为他年龄小不能天天步行往返,11岁的他便背上铺盖当了住校生。那时节中国大地上的3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家里缺衣少粮,他每个星期六回家,背18个蒸馍,星期天天黑前赶到学校,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中、晚饭,顿顿全吃白开水泡馍。唯一的佐餐品就是从家里带点儿食盐,每顿吃白开水泡馍时用筷子头蘸一点食盐加进去。最奢侈的是偶尔从家里带些干辣椒面,吃饭时给白开水泡馍里加一点,那就是过年般的享受了。可辣椒却有促进胃肠消化的功能,使得他胃口大开,平均一顿一个蒸馍压不住饥饿,有时就不由得多吃一个半个。但带的馒头总数有限,这顿吃了下顿就得少吃或不吃,饿了也只能硬撑着。长期的食物单调且营养不良,使正在长身体阶段的他过分消瘦,饥饿常使他头昏眼花,有一次竟昏倒在地。同学们扶他起来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脸色惨白无言以对。
那段时间,他姐姐在家里缺衣少粮的情况下,每次蒸馍馍总是预先留够他的18个馍馍,其余的才留给全家人。有一年青黄不接的时节,他从家里背到学校去的榆树叶粉和面捏成的蒸馍到星期四就长出了黏乎乎的白丝丝,掰开馍馍白丝丝扯得老长也断不了,他只好向老师请假回家换馍。当他忍着碌碌饥肠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回到家时,只见全家人都躺在土炕上,原来家里已断粮好几天了!听他说把馍馍带回来了,也顾不得发霉变质,拿出来在铁锅里加上水热透了,狼吞虎咽般分着吃了。
那天晚上,他独自走到茅屋外的苦楝树下,抚摸着挺拔的树干,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他觉得自己之所以那样喜欢苦楝树,恐怕是因为自己的苦命和苦楝树的苦味有某些相似之处的缘故。
1966年,张兴初中毕业了。由于家境贫寒,他当时没有报考高中,而是报考了一所中技学校(中技学校不收费),虽然这所中技学校录取了他,但由于“文革”开始了,他就无法进校学习,只好辍学回家务农。
可他是个勤于观察、善于思考的有为青年。他发现自己家茅屋外的苦楝树以及周边庄稼地的苦楝树下,即使是炎夏酷暑,湿热蒸腾,只要有苦楝树叶遮蔽,蚊蝇、小虫很少来树下烦人。许多当地农民一见菜地里有虫子为害,就折几把苦楝树枝扔在地里,常常会起到灭虫的效果。
这类事儿诱发出他极大的兴趣。他折来苦楝树枝放在口中咀嚼,除了感到苦涩外再也无法深入探索。每逢阴雨连绵无法作务农活时,他总喜欢躺在土炕上琢磨这些事儿。可最终他还是失望了。因为他感到自己所学的知识还远远不足以搞清其中的奥秘。
然而,机会终于降临到他的身上,而且是那样神速、别无选择又极具传奇色彩。
那是1972年春天,推荐上大学的难得机遇,竟然降临到他这个很少有人注意的人身上。全乡只有一个名额,他也不明不白地超越众多的“对手”被选中进入当时的西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实现了他5岁那年的“口彩”。
这是张兴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当他极其顺利地坐进西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植物保护专业的教室里,他才觉得这段时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是真的,不是梦!他也才得知这里人才济济,名家辈出,是全国有名的农业“花园学府”之一。他想,命运有时还真有“天遂人愿”的时候,自己正苦于探索植物杀虫奥秘不得要领、难以问津而无法进展时,自己竟鬼使神差地真有这么一个学习植物保护知识的机会。植物保护,顾名思义,肯定是学习和研究植物保护知识和技术的。因此,除了认真学好每一节课,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不论大本小本、厚本薄本,只要他觉得可能和植物保护沾边,抱起来就啃,尽情地咀嚼、吸吮着科技知识,同时记下了一本又一本笔 “苦楝又名楝树,楝科,落叶乔木,高可达20米,春夏之交开花,花淡紫色,圆锥状聚伞花序,花丝合成细管,紫色,核果球形或长圆形,熟时金黄,俗称金铃子。因其子小如铃,熟则金黄,故名。主要分布在我国山西、河南、陕西以南地区。印度及东南亚亦有分布。多生于低山、平原。最喜光,生长快。木质坚硬,易加工。可供家具、乐器、建筑、舟车、农具等用。种子供药用。花、叶、树皮、根皮亦入药。又为行道树、观赏树及海防林树种。它高大,树干直,浓荫如伞,树冠舒展飘逸。开花时节,香而有苦味,因而香得特别,香得持久。亦能在秦岭及其北麓生长。秦岭北麓一带人称这为‘苦苦树’。这是因为,生长在秦岭北麓及其丘陵地带的苦楝树,因昼夜温差大、体内贮存的水分少,因而划破树皮流出的汁液特别苦。而环境条件愈差,树皮流出的汁液也就益发苦不堪言。
苏东坡在《格物粗谈》中写道:端午取苦楝子,碎投厕中,不生虫。
“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楝花铺席下,杀蚤、虱……
哦,苦楝树下走出的张兴,时刻没有忘记对苦楝树的深情。他清楚地记得,当他背着铺盖上大学时,是手抚苦楝树干、眼含热泪、怀着深厚的眷恋之情离开家乡那片生他养他的一方水土的。当时母亲已年过七旬又体弱多病,父亲已80高龄,腰身佝偻,风烛残年。两个哥哥当了“上门女婿”,寄人篱下,姐姐已经出嫁,另一个哥哥成家后已分家另住……。两个老人谁来照顾?这是他的最大担心。多亏了古风淳朴厚道的家乡父老乡亲答应帮衬,他才得以一步一回头地踏进高等学府的大门……
哦,走出图书馆的他,来到校园里的一棵苦楝树下,抚摸着它干瘦但却硬朗的树干,被它的可贵的品格深深感动了!
很快,张兴大学毕业了。由于他品学兼优,经过学校层层选拔,他被留校任教。苦楝树下走来的张兴,走上了大学讲台。
1977年,和煦的春风吹化了冰封许久的祖国大地,历经磨难的人民共和国,重新恢复了大学招考制度。1978年,又恢复了研究生招考制度。看到这一喜人景象,张兴不由得动了心。他一边认真工作,一边不失时机地进行报考研究生的准备。
1979年9月,经过严格考试筛选,张兴考中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昆虫毒理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委员赵善欢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攻读方向为昆虫毒理学。
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张兴盼望着自己能考个好成绩,争取被录取。当正式录取通知书拿到手上时,他是又喜又愁,悲喜交加。喜的是终于如愿以偿考中硕士,悲的是年老的母亲和妻子儿子在农村老家,生活清苦不说,自己远去华南,他们谁来照顾?更何况,自己翻遍所有衣袋,连买一张去华南读学位的火车票的钱也凑不够。这个状况,自己的家人生活怎么办?
越想越愁,越想越难,经过无数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平静下来,他打定了主意——放弃读硕士。
硕士报到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张兴没有一点动静。他周边的老师和同事们都感到奇怪。一个个用询问的眼光看着他。他只装作没看见,仍然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备课、准备实验、做实验。
硕士报到的日子已经过去了10多天,他仍然无动于衷。老师和同事终于忍不住了,问他怎么还不去报到。他淡淡地回答:“不去了?”有的人好心地劝他,他不为所动。有的人也表示支持他的选择,但又表现出各种婉惜之情。
这天夜里,系党总支书记王建邦老师猛然推开了他住的宿舍门。当时他正在灯下备课。
王建邦书记手里拿着一沓钱,语重心长地对张兴说:“我知道你的脾气,也知道你的性格。你是个硬汉子,宁折不弯。从来都不肯张嘴求人。你之所以至今不去报到,是因为没有买一张车票的钱。”
王建邦书记拿着那沓钱对他说:“我替你写了份困难申请,从系里和学校领到130元困难补助款。我知道你的硬气劲,所以替你签的字。你知道,系里困难补助的最高额度是30元,学校困难补助的最高额度是100元,合起来就这么多。但可以帮你解决买一张去广州的火车票。你还是去吧,机会实在难得啊!学校支持你去深造,没有别的要求,只是希望你毕业后能回来工作。你清楚,咱们缺化保老师啊!”
听到这里,张兴的双眼湿润了,他咬了咬嘴唇,十分矛盾地接过王建邦书记递过来的130元钱,紧紧握住王建邦书记的手,眼泪再也止不住了,顺着腮边一串串流了下来,一句话也说不出。
山重水复疑无路
张兴挟着一身大西北黄土高坡风沙黄尘来到华南农业大学昆虫毒理研究室不久,以治学严谨、要求严格、待人严肃的“三严”作风而著称的赵善欢教授慧眼识英才,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敏而好学、纯朴执着的北国青年张兴。
在羊城求学深造的头3年,张兴很少回家。一则是由于自己的确囊中羞涩,拿不出多少钱买火车票;二则是由于他在研究实验中发现某些植物对害虫有致其拒食和不能正常生长发育的作用。他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个富有魅力的自然之谜。似乎是一种直觉,他朦胧中觉得苦楝很有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植物。但科学研究是十分严肃、严谨、严格的,来不得半点“想象”和“跟着感觉走”,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试验材料和科学数据。为此,他住进实验室,以便于观察、分析、试验,同时也为更节约时间。他还在几小片空地上种了些青菜,自己抽暇在实验室做饭吃,可以节省点费用,省下尽可能多的钱寄回家里,贴补家用,养家糊口。而此时,他的父亲已经过世,垂暮之年的老母亲长年卧病在床,只字不识的妻子任凤香除了侍奉老母亲,还拉扯着一对儿子……
当赵善欢教授耳闻目睹了张兴的这些情况后,不禁感慨万千,对这个勒紧裤带孜孜求学的上进青年更加青眼相看,更加悉心地指导。
在斡旋硕士论文阶段,张兴看到国内外刊物尤其是国外刊物上关于印楝的研究报道很多,便选择印楝作为主攻目标。因为印楝是世界热门植物,已经取得较大研究进展,并召开过好几次印楝国际学术会议。
但是,必须亲自做实验,才能作出最后的结论。通过一段时间的实验研究,他得到的数据证明,印楝中的印楝素药用效果最为理想。在印楝素对昆虫致毒机理的研究中,他所得到的“其为一系统性致毒作用”的结论,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重视与认可。这一点,也与国外众多的研究结果趋于一致,极富开发价值。可是,此时他却发觉自己走投无路了!
原来,印楝主要在印度及东南亚各国广泛分布,属亚热带树种,非洲及南美洲也有分布,但在我国尚未发现真正的印楝树种。他亲自参加了此前海南和广东的印楝引种,一者数量远未形成规模,加之引进的印楝树树种树冠生长太大,不抗台风,多年后宣告失败了。而国外的印楝研究早已捷足先登,美国已有印楝杀虫产品登记注册,印度的印楝产品也已进入国际市场。如果我国步此“后尘”,落后一步不说,仅原料进口一项,其费用之高已不难想象。
一下子,赵善欢教授和张兴都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之中。
此时的张兴,仍然住在实验室中,除了做实验,还是自己种菜,自己做饭。而此时的广州早已不是数年前的广州,消费水平之高,更不是他的工资水平所能承受得了的。那时节,他每月只有52元工资,而且需要用购粮本去买。为了生存,他只好硬着头皮借家在广州的同学或老师的粮本,去购买当地最便宜的面饼,勉强维持……
生活的困窘加上事业上的困窘,两面夹击着张兴这个从北国苦楝树下走来的汉子,他陷入徘徊之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天夜里,他独坐灯下,陷入苦苦思索之中,不知不觉间伏在书桌上,朦胧中又一下子惊醒,一道灵光闪过脑际,他想到是否可用川楝代替印楝?想到此,他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和轻松感,急于想找赵善欢教授交换意见。当他一头冲进室外浓浓的夜幕之中时,才意识到半夜已过,太晚了。借着路灯看一下手表,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兴奋异常又急不可耐的张兴只好重返实验室,在一沓稿纸上盘算起下一步的研究方案来。
其实,此时的赵善欢教授同张兴一样,也无法入睡。这段时间,赵教授同张兴一样焦虑。也许是一种心灵感应或“英雄所见略同”吧,赵教授也想到了用川楝作为印楝的替代品,在中国开发植物源农药。他此时也正急于想找张兴交换意见,也同样是因为夜已过于深沉,未去打搅。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张兴一步冲进了导师赵善欢的寓所。师生二人一见面,抛却了惯常的礼仪,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同一个思路——真正的“一拍即合”!
可张兴却怎么也没有料到,他又一次陷入两难境地。
人的思维,常常有一种“定势”。张兴这次研究与探索的曲折与坎坷,可以说是人的思维定势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影响所致。
按照国外和他自己从印楝果实中提取和研究印楝素的方法,他花了将近一年半时间,从我国广泛分布的苦楝、川楝的果实和叶子中提取杀虫物质,同时配制了一批杀虫试验品。可是费尽千般周折、万番艰难,他不仅未从中找到印楝素,而且提取物的杀虫效果也不理想。用苦楝和川楝替代印楝的思路,几乎化为泡影。他又一次陷入困境之中。
科海探险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珍。经过一番艰苦的探索、分析、试验和研究讨论,张兴果然不负导师赵善欢教授的重望,接连在国内外有关刊物上发表了植物源农药研究方面有分量的论文,引起学术界同行的普遍关注。
但是,凡是张兴与导师赵善欢教授共同署名发表的论文,稿费赵教授一分都不肯要,全给了张兴这位有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的高足。以至由此以后,张兴每一忆及或谈及此事,就禁不住无比动情地遥望南天,摘下眼镜,一遍遍地擦拭镜片!
糟糠之妻不下堂
随着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有名的羊城广州,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议论中,即使是在张兴的家乡陕西周至县集贤村,虽是穷乡僻壤,却也议论迭起。原因是张兴在广州,不仅很少回家,竟连书信也少见。有人交头接耳说张兴忘了任凤香。有人说任凤香大字识不了一箩筐,土得掉渣,张兴是研究生,早就想甩了另娶。何况如今远走高飞,到了广州那“花花世界”。有的甚至说在广州亲眼见张兴手挽相好的,连孩子都抱上了。
谎言说过三遍,就有可能成真。这些风言风语越说越真,竟连死活都不肯相信的任凤香也有点相信了。她无论怎样也在家里坐不住了,下决心南下广州去找她的“陈世美”。学一学当年的“秦香莲”。
她含着满眼的泪水,在灯下给张兴赶缝了“最后一套衣服”,牵上小儿子,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南下的火车上坐着任凤香和小儿子。小儿子不知道大人的心思,早就睡着了。可任凤香却仍然心潮起伏,不知此行是福还是祸,因而难以平静。她觉得张兴是大学生如今更是研究生,自己能跟他过这么多年日子已经知足了。而自己为张兴侍奉老人,生育两个儿子,缝补洗理,撑持家务,也算对得起张兴。自己虽不识字但却懂礼。此行一是为了探个究竟,以了却心中渴念,二是平息一下自己心头的忐忑。如果传言是真,自己不会真像秦香莲那样去找包公断案,而是给张兴留下一个儿子转身就走……
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抛头露面去广州。心急如焚的她顾不得欣赏沿途南国风光,悄没声息径直来到华南农大,轻手轻脚地推开了昆虫毒理研究室的大门,朝里探头一看,室内仅是张兴一人正在挥汗如雨地忙碌着赶写文章,不见有什么女人、孩子之类。
正在专注地埋头写作的张兴猛一抬头,见是妻子和小儿子站在自己面前,高兴地一下跳了起来,揽过小儿子亲个不够。
妻子不冷不热:“不认得?”
张兴不明就里:“咋不认得?”
夜晚来临,任凤香留了个心眼。张兴着意为她安排的住处她死活不去,非要“守着”张兴。其实是想看个“究竟”。心想自己绝不是那个秦香莲。
一连3个晚上过去了,一切平静得出奇。只见张兴每天从早到晚只顾拼命工作,并未见有什么“公主”、“阿妹”的上门来打搅。任凤香疑惑不解。有天夜里便不冷不热地问张兴:“是不是我们娘儿俩来了,你那相好的不敢露面了?”
“啥相好的?”张兴一头雾水,莫名其妙。转念一想,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妻子带儿子此行来到华南的用意,不禁朗然而笑:“你想到哪里去了!相处这么多年,你还信不过我?”
“那你为啥连着几年都不回去?”妻子毫不放松,紧追不舍。
张兴一听,低下了头:“没有钱呀。与其把钱都交给铁路和火车,倒不如寄给家里让你和娘、孩子们过得宽余点。”
一提到钱,妻子似乎理解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张兴每月的工资有多少钱,她当然清楚。但她仍有疑云:“那写封信回去总可以吧?”
“写信?写信不是明摆着为难你和家里人吗?再说我也忙,事儿太多,又何苦让你们作难呢?”
说到这儿,妻子听到的所有风言风语和猜疑顷刻间冰释了。自己只字不识,母亲更是如此,两个孩子都小。真要有信,还得求人念给她听,多难为情。
理解出真情。亲眼看到张兴对自己及全家人的一片爱怜、体察之心,作为一个妻子,只有更加敬护张兴的分儿。
任凤香与小儿子在张兴那儿住了半个月之后,不顾张兴的再三挽留,执意要带着小儿子返回。家里还有一老一小两口人让她无时无刻不牵挂和忧心啊!加之张兴太忙,她不忍心为自己和孩子让张兴分心,何况老婆母有病在家,自己出门多日,老人家肯定也是忧心如焚啊。
张兴送妻子和小儿子来到广州火车站,妻子和儿子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列车停在站台上尚未启动的那一刻,任凤香从车窗口伸出头来低声对张兴说:“我看你师兄师弟们每个人身边都有个年轻漂亮的大学生、研究生作伴。你一个人在广州太孤单、太可怜。你如果愿意,给我句话就行。我不怪你。能和你过这么多年,我知足了。”
一声汽笛长鸣,铁轮隆隆启动,越转越快。张兴只觉得月台和自己的身体在同时颤动,喉咙哽咽,眼圈潮湿。他随着火车的加速,追赶着妻子和儿子所在的车窗口:“你别胡思乱想。你替我上养老母,下育儿子,我才能安心读书,静心研究。你要一句话,我就给你一句话。我们要过一辈子!”
妻子扶着车窗,泪水奔涌而出,泣不成声。
铁龙轰鸣着驰向远方!
倚天万里须长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清晨,一辆满载着几千斤鲜嫩黄瓜的拖拉机驶进某市一家蔬菜市场。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时间不长,吃了这家卖的黄瓜的人,有数十人丧命,数百人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医院的化验结果表明,这些黄瓜上市之前刚刚喷洒过有机磷剧毒化学农药……
某年夏天,一对新婚夫妇到南方某城市度蜜月。当他们旅途中口渴难耐时,便就近在一个蔬菜摊上买了几斤鲜红的西红柿,用卫生纸擦了擦便吃了起来。可他们还未返回所住的旅馆,两人相继栽倒在大街上。经路人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检查,发现他们两人的胃中尚未消化的西红柿中含有剧毒农药……
看到这些报道,作为研究新型植物源杀虫剂的张兴心里真不是个滋味,不由得从心里更加铆足了劲儿。
新型植物源杀虫剂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才兴起的世界性热门研究课题。张兴的导师赵善欢院士1979年赴德国参加了这方面的世界专门会议,受到很大启发,并紧紧抓住机遇,回国后在我国科学界首次提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研制新一代无残毒农药势在必行。要想不让类似悲剧发生,要想让我国人民延长寿命、后代聪明、生活幸福,要想让我国瓜果蔬菜跻身世界市场,在农药研制、植物保护方面必须先行一步,必须要有这个超前意识。
因此,在赵善欢院士的指导下,张兴将他的硕士研究论文题目确定为《楝科植物杀虫剂对几种害虫拒食和抑制生长发育的作用》,并尽力加快研究进度,查资料、找药典、做实验、取数据、摄实物……夜以继日,孜孜以求。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苦心孤诣地探索,张兴终于摸清了楝科植物对某些害虫具有抑制其生长发育、改变其味觉器官的感觉而对农作物产生拒食作用等机理之所在。当年在故乡的苦楝树下发现的有趣现象,在科学之光的映射下,现出了清晰的逻辑关系。因而当他登台毕业答辩时,那严谨的科学依据、大量的实验数据、翔实的试验材料、真实的实物照片、流畅的叙述文笔,令答辩委员会的专家教授们大为赞赏,一致同意评为优等,并在华南农业大学全校研究生和导师大会上作了论文答辩示范讲演。
眼看着这位刻苦自励、勤奋好学、科学求实而且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得意弟子戴上硕士帽即将告辞北归的时候,学识渊博而又以“三严”著称的院士赵善欢教授动心了,与弟子张兴展开了一场“攻心战”——专门约张兴到自己办公室谈话。
张兴估计导师可能与自己谈未来的动向。但他也知道,导师太忙,谈话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在平常,赵院士不论与谁谈话,最长也没超过20分钟。张兴清楚地记得,与赵院士同一列火车赴前苏联留学的一位同行和同学,因多年未见,前来找赵院士,赵院士只答应谈5分钟时间。结果真的就只谈了5分钟。
没想到,导师这次与自己的谈话破天荒地超过了4个小时——整整一个上午!
张兴来到导师办公室,赵教授开门见山,劈头就问张兴:“硕士毕业后有何打算?”
“回我的母校去!”张兴的口气毋容置疑,也不假思索。因为在此之前,赵先生也曾多次对他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他一直都是这样回答的。
“不可更改吗?”赵教授再次逼视着张兴。
“似乎没有什么可更改的。”面对严师的锐利目光和咄咄逼人的气势,张兴的口气稍有改变,但仍绵里藏针。
赵教授板着面孔,给他指出了3条出路,供他选择:1,留校——留在华南农业大学任教;2,分配去广东昆虫研究所工作——因与华南农业大学不远,两边联系和合作方便;3,马上送你出国,暂时不毕业——这可免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张兴心想,留在华南农业大学,留在自己尊敬的导师身边,留在南方大都市,这无疑是自己这辈子的福分,求之不得。但他忘不了故乡的苦楝树,忘不了离开西北农大前夕学校和系里领导、同事的依依深情。尤其是王建邦书记替他写困难补助申请并代他签字领取,雪中送炭般及时送来130元钱,才促使他最终下决心南下羊城。更何况大西北广袤而辽阔,急需一代代人才尤其是科教人才在此扎根、奉献和建设。出国也算一条路,当时很多人都是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的好事。但他觉得从事植物源农药研究,在国内搞比去国外学更便捷。这一点,导师比自己更清楚。因此,导师所说的三条路,其实说到底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留在华南。如果这样,他将无颜面见西北父老和自己的母校。因此,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恩师说:“我还是得回西北去,我的根在西北。”
赵教授不解地问:“岂不闻‘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不等张兴接话,赵教授又说:“你是不是担心你爱人和大儿子的工作安排?这个,我已替你想过了。华南农大会作出很好的安排。”
见张兴并没有答应的意思,有点出乎自己的意外——因为在当时,能安排农村户口的妻子和儿子两个人到一个大城市工作,那简直是天大的好事,无论是谁都会感激涕零的,而张兴似乎没有动心。赵教授接着说:“这个事你尽管放心。作为一校之长,我说话岂能不算数?”他似乎觉得张兴可能不大相信这事儿能办成。
张兴:“赵老师,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担心西北……”
赵教授不等张兴把话说完,断然地打断了张兴的话头:“这个你不用担心。西北农业大学不同意的话,我来做工作。你对母校有感情,我不让你出面。”
见张兴仍未答应,赵教授略一思忖,又说:“这样吧,我现在就给农牧渔业部领导打电话,让农牧渔业部领导出面先做做你母校的工作。”说着,不等张兴答话,就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要通了农牧渔业部,说明自己的研究室需要将张兴留下,请求部里出面做做西北农业大学的工作。张兴隐约听电话里不知是部里哪位领导似乎已经满口答应了。
张兴的头脑十分清醒:“赵老师,我,我不大适应这里的气候……”
赵教授不以为然地:“气候?你在这里3年了,气候不是问题!你妻子和两个儿子,来了后也会慢慢适应的。在华南工作的北方人多得很,哪个不适应了?”
张兴:“我母亲恐怕是难以适应的。”
“我知道你是个大孝子。老人的事,实践了才能下结论。别把结论下得太早了!”赵教授没想到张兴会这样执拗,不由得动了怒,终于和他“翻了脸”。
最后经农牧渔业部出面从中调停,才达成了一项折中的方案,由西北和华南两个农业大学共同签署了一份合同:张兴必须每年半年在西北农业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另外半年时间在华南农业大学从事新型农药研究。在两所大学的身份都是教师。签署日期为1982年10月。
1983年2月底,张兴带着南国求学的丰厚收获,一头扑进了魂牵梦萦的苦楝树下大西北黄土地的怀抱。手抚故乡的苦楝树,张兴在心里默默地与黄土地对话:你的儿子回来了!
在西北农业大学,张兴一边代课,一边探索,研究更加艰深的课题。然而,“初学三年剑,泰山不可当。再磨三年后,不敢试锋芒。”他原以为3年硕士学习,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以后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工作,不会有太大的障碍。然而,事实却让他一次次失望,他越来越深刻地体味到,自己仍然需要知识的补充。因此,他就进一步拼命地汲取知识的营养,认真备好每一节课,同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不断地开阔自己的视野。
他回到西北时,已经离春节很近了,只剩两三天时间。可大年初一刚过,他就一头扎进办公室和实验室,又是备课,又是做实验,还要加班加点整理论文。到这时,他才真正心领神会了“活到老学到老”这句古训的深刻含义。
第二年7月,他刚代完西北农大应代的课,又立即启程南下,按照两校的合同,去华南农业大学履行另一半诺言,继续开展新型杀虫剂的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张兴研究新型植物源杀虫剂,最初是从苦皮藤、雷公藤、鱼藤、黄杜鹃等植物的筛选开始的。经过对众多植物杀虫活性物质生物活性测试,并对其有效成分的对比试验和分析其效价及开发应用前景的过程中,先后筛选了150多个植物品种,其中有开发价值的就有近二十种。其中楝科10多种,还有豆科、桉树等。在1984年召开的全国植物源杀虫剂专业学术会议上,他讲述了自己在赵善欢院士指导下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与关注。
1984年3月,他又得返回大西北,履行自己的另一半诺言。而当他站在家人和同事面前时,人们已不敢认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脸瘦如刀背,身型像细虾……,简直成了另一个人!
原来由于前段时间在华南,时间紧,任务重,他的研究“胃口”又过于大,简直忙得他焦头烂额,饭是有一顿没一顿,又天天熬到深夜,身体怎能不垮?
为了能在赵善欢院士指导下悉心从事新型植物源杀虫剂的研究,也为了进一步给自己“充电”,他决定听从恩师的劝告,报考赵院士的博士研究生。结果一考即中。此时,西北农业大学决定送他出国深造读博士。面对又一个“两难”选择,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选择了在国内读博士学位。为了深造、工作两不误,也为了防止再有新的“麻烦”,他决定放弃读全脱产的博士研究生,而自动请求读在职的。后经当时的农牧渔业部再次从中协调,并发文确证,才终于办成了。许多人对他的这一系列“选择”大或不解,他的理由却很简单:力争在祖国的土地上拿出属于中国人的新型植物源杀虫剂!
1985年7月13日,他带完这一年在西北农大的最后一节课,于7月15日再次南下华南。
一到华南农业大学就拜见恩师赵善欢院士,他不等喘一口气,对恩师提出了自己的3点想法:一是继续从事楝科植物杀虫剂的研究;二是研究几种新发现的豆科植物杀虫剂;三是攻下利用烟草工业废料研究植物杀虫剂的难关……
独具慧眼的赵善欢院士不等弟子讲完,双目放光,满意地看着自己的得意门生,当即决定:继续从事楝科植物杀虫剂的研究,杀出一条血路来,唱一曲中国人的志气歌!
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他发现我国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利用川楝提取物驱蛔虫。由于当时我国医疗卫生状况较差,人们也不大讲究卫生,约有70%的人感染了蛔虫。起初人们只知道利用中草药山道年驱蛔虫,后来周恩来总理指示重庆中药研究所研制中国人自己的驱蛔虫新药,科研人员经过艰苦探索,发现川楝树皮中提取的川楝素驱虫效果特别理想,便动员四川等地发展川楝种植业,1955年即开始工业化生产,很多小厂都可生产这种驱虫药片。
责任编辑:江志利